空余上,耐得住的咀嚼和吟哦
孔金泉
相传,北宋哲宗绍圣四年,苏轼再次被贬,前往儋州时,途经贵州赤水河畔四方井村。一时苦闷,遂使寻酿,酒入愁肠,欲泼墨一吐心中的郁愤,但仅书“空余上”便一醉不醒。也给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苏轼妙笔,意出言外,他接下来的笔墨会走向何处?后人只能臆测,不敢狗尾续貂。千年以后,有酒借了“空余上”的皮囊,但持觞,似有抵达之味。以酒释文,于匠心做足工夫,也算是异曲同工之妙吧!
何谓“空余上”,搜索,仅见李煜“秦楼不见吹箫女,空余上苑风光”。但此“空余上”似与彼“空余上”不搭界也。既无定论,反倒给了我诠释的空间,也算是向苏轼致敬。
这个世上的人皆求圆满,人们讨彩头也喜欢把话说得满满当当,非富即贵。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,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,所以有了期许。人有旦夕祸福,月有阴晴圆缺,遗憾恰恰是这个世界的日常。唯是日常,便望向圆满,给自己画了一张饼。
但画画的人不这么认为。以画虾独步中国画坛的齐白石,画面上的虾空无所依,不见水而处处是水。这就是留白的艺术。唯其空,反倒有了余地,给了想象的空间。有人说中国画与西方画的本质区别即在于中国画求“意”西方画求“形”,所以你看中国的山水画,不求形似,但求意境。讲究气韵生动,妙在似与不似之间。文人画甚至抛弃了色彩,但细细究去,又墨分五色,有深浅浓淡之别。这也是空余,便于观者的跟进,倏尔悟得。
作诗也是这个道理,唯恐遗漏了什么,所以在笔墨上倾囊而出,是作诗的大忌。诗在言外,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和附着物,真正的诗意却蹁跹云外。郦波教授最喜欢的一句诗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年龄的包浆总要是到若干年后,才能懂得这首诗的深意。正如王世贞言:“然不解则涉无谓,既解则意味都尽……”
又如顾城的诗,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正常的意象却有深思的魅力。只是用意象、用隐喻,在浓重的黑色背景上凸现了一双不同寻常的“黑色的眼睛”,却让人隐约见到了一束白光。其高标之处都在于它的空余,言未尽而意无穷。
走进一片雨林是让人窒息的,但一片林中空地,就会让人眼前一亮。它是森林动物的乐园,亦给了森林盎然的生机。
《菜根谭》是本谈论人生趣味的书,其中有言:“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,忙时要有悠闲的趣味。”人生就是为了赶路吗?我觉得路上的风景更为重要。给自己留出空余的时间,“且停亭中停一停”,便可以等到灵魂。丰子恺便是这样一个人,他去杭州,坐车只需三个小时,他却偏偏走水路,动辄两三天。于别人是苦,于他却兴味满满。生活需要一个缺口,空余即是圆满。所以说空余为上!
一杯空余上,含珠吞玉间,我似乎听到了它的吟哦!此中真意,欲辨忘言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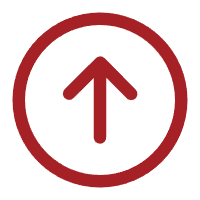


 收起
收起